海上扁舟
《海上扁舟》(英語:The Open Boat)是由美國作家史蒂芬·克萊恩(Stephen Crane)創作的一篇短篇小說。該書於1897年首次出版。克萊恩早年曾前往古巴擔任報紙記者,在佛羅里達州海岸遇到了一次海難並成功逃生。這本書就改編自他的這個海難經歷。當時克萊恩乘坐的海軍准將號蒸汽船在撞上沙洲後沉沒,使得他在海上被困了三十個小時,最終他和另外三人不得不乘坐小船前往岸邊。同行中有一位名叫比利·希金斯(Billie Higgins)的加油工在小船翻覆後溺水身亡。克萊恩將這次海難和倖存經歷記錄下來,名為《史蒂芬·克萊恩的親身經歷》(Stephen Crane's Own Story),於他獲救幾天後首次發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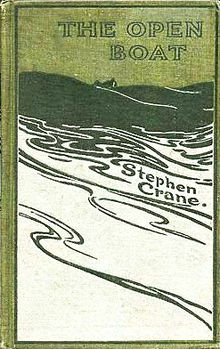
克萊恩隨後將他的記錄改編成敘事形式,由此創作出短篇小說《海上扁舟》並發表在《斯克里布納雜誌》上。該故事以一位匿名記者的視角敘述,這也就暗示了克萊恩是這個故事的真實作者。故事情節與克萊恩本人的海難經歷非常相似。1898年,名為《The Open Boat and Other Tales of Adventure》的美國版本發行;名為《The Open Boat and Other Stories》的版本也同時在英國發行。該故事因其創新性而受到當代評論家的稱讚,被認為是自然主義文學的典範,也是克萊恩經常被討論的作品之一。該故事以其對意象、諷刺、象徵主義的運用和對生存、團結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衝突等主題的探索而聞名。H·G·威爾斯評價《海上扁舟》「毫無疑問是克萊恩所有作品中的巔峰之作」。[1]
背景
編輯1896年除夕夜,25歲的史蒂芬·克萊恩登上了海軍准將號蒸汽船。他此次出行是受巴切勒報業集團聘用,去擔任古巴獨立戰爭期間的戰地記者。該船從佛羅里達州傑克遜維爾出發,船上乘客二十七八人,並載有供應給古巴叛亂分子的物資和彈藥。[2]在聖約翰河上,距離傑克遜維爾不到3公里的地方,海軍准將號在濃霧中撞上沙洲並損壞了船體。雖然船隻第二天被拖離沙洲,但它又在佛羅里達州的梅波特擱淺,並造成進一步受損。[3]那天晚上,鍋爐房開始漏水,由於水泵故障,船隻停在距離蚊子灣(現在的龐塞德萊昂灣)約26公里的地方。隨着越來越多的水湧入船內,克萊恩形容引擎室混亂得好似「冥王哈德斯的廚房」。[4]
1897年1月2日凌晨,海軍准將號上的救生艇被放下。早上七點,船隻沉沒。克萊恩是最後一批搭乘救生艇離開的乘員。在他們試圖登陸代托納海灘前,克萊恩和另外三人(包括船長愛德華·墨菲)在佛羅里達州海岸漂流了一天半。然而,小船在海浪中翻了,早已精疲力盡的他們不得不自己游到岸邊。其中一位名叫比利·希金斯的加油工在這個過程中遇難。[5]這場災難占領了當時全國各大報紙的頭條。有關該船遭到破壞的謠言也廣為流傳,但從未得到證實。[6]
這場災難發生幾天後,克萊恩與他的妻子科拉重聚。他利用在傑克遜維爾等待另一艘船的間隙時間迅速寫下了關於沉船事件的初稿。由於急需一份工作,克萊恩不久就前往紐約,尋找能參與報道即將爆發的希土戰爭的工作機會。幾周後,大約在二月中旬,克萊恩完成了故事的撰寫,也就是後來的《海上扁舟》。[7]據記者拉爾夫·德拉海·潘恩介紹,克萊恩再次經過傑克遜維爾時,他給船長墨菲看了這篇短篇小說的初稿。據說當克萊恩詢問他的意見時,墨菲回答說:「你寫得很好,史蒂芬……這就是事情的經過,就是我們當時的感受。再多講些給我聽吧。」[8]
劇情概要
編輯他們誰也不知道天空的顏色。他們平望過去,緊盯着席捲而來的波濤。這些波濤是藍灰色的,只有浪峰處噴濺出白色的泡沫。地平線時寬時窄,時沉時浮,邊緣被像岩石一般尖銳凸起的浪花勾勒得參差不齊。[9]
《海上扁舟》分為七個章節,每個章節都主要從一個記者的視角講述故事,也就是以克萊恩本人的視角。第一節介紹了四個人物——記者(旁觀者,與船上其他人關係疏離);[10]受傷的船長(因失去船隻而傷心,但具有領導能力);胖且滑稽的廚師(始終樂觀地認為他們能獲救);加油工比利(最強壯的人,也是故事中唯一提到名字的人)。故事開始於一場沉船事故發生後,他們四人作為事故的倖存者,乘坐着一艘小救生艇在海上漂流。
在接下來的四個章節中,他們的情緒從自己身處絕境的憤怒,變成逐漸理解並同情彼此的處境和感受,他們還領悟到了自然對人類命運的冷漠態度。他們變得疲憊不堪,彼此爭吵不休。儘管如此,加油工和記者仍在輪流划槳朝着岸邊前行,而廚子則不停舀水排水以保持船隻漂浮不會沉沒。當看到遠處地平線上出現一座燈塔時,他們心中燃起了希望,但又對前往燈塔所要面臨的危險望而卻步。他們看到了岸邊揮手的人以及那艘不確定是真是假的船,卻無法取得聯繫,這讓他們的希望進一步破滅了。記者和加油工繼續輪流划船,其他人在船上輾轉難眠。隨後,記者注意到一條鯊魚在船附近游動,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並沒有受到影響。在倒數第二節中,記者疲憊地回想起卡羅琳·諾頓夫人的詩《萊茵河畔賓根》中的一節,講述的就是一名「軍團士兵」遠離家鄉並死去的故事。
在最後一節的開頭描述到,四人決定放棄他們已經待了三十個小時的搖搖欲翻的小艇,試圖游到岸邊。在這段長途游泳的過程中,四人中最強壯的加油工比利游在最前面;船長一邊扒着船脊一邊朝岸邊前進;廚子利用倖存的槳向前划動;記者被一股水流困住,但最終還是脫困成功繼續前進。在其中三人安全到達岸邊並得到一群救援人員接應後,他們發現比利已經死了,他的屍體被衝上了海灘。
文章主題
編輯人與自然
編輯與其他自然主義作品類似,《海上扁舟》審視了人類的處境:人不僅與社會隔絕,還與上帝和自然隔絕。人與自然之間的鬥爭是作品中最明顯的主題。[10]雖然故事一開始書中人物認為洶湧的大海是針對他們的敵對力量,但他們逐漸相信自然是冷漠的。在最後一節的開頭,記者重新思考了他對自然敵意的看法:「個體奮鬥中的自然是寧靜的——風中的自然,以及人類眼中的自然。在他看來,自然既不殘忍,也不仁慈,也不狡黠,也不睿智。但她是冷漠的,絕對冷漠的。」[11]記者經常用女性代詞來指代大海,這讓船上的四名男子面臨着一種無形但女性化的威脅。評論家莉黛絲·基桑(Leedice Kissane)進一步指出這個故事似乎是對女性的貶低,這四個倖存者將命運擬人化為「一個愚蠢的老太婆」和「一隻老母雞」。[12]克萊恩的其他作品中也出現過「自然最終是冷漠的」這一觀點。克萊恩1899年的詩集《戰爭是仁慈的》中的一首詩也呼應了克萊恩作品中常見的宇宙冷漠主題:[13]
| 原文 | 中譯 |
|---|---|
| A man said to the universe: "Sir, I exist!" "However," replied the universe, "The fact has not created in me A sense of obligation." |
一個人對宇宙說: 「先生,我存在!」 「但是,」宇宙回答說, 「事實並沒有讓我產生 一種義務感。」 |
由於人類的孤立而產生的形而上學的衝突也是整個故事的重要主題,因為人物不能依靠更高的信仰或存在來保護自己。[14]記者感嘆缺乏宗教的支持,也無法將自己的不幸歸咎於上帝。[15]他沉思道:「當一個人意識到自然並不認為他重要時,認為即使沒有他,宇宙也不會因此而受損時,他開始想要向神殿投擲磚塊,結果他痛心疾首地發現這裡既沒有磚塊,也沒有神殿。」[16]人對自己和周圍世界的感知也不斷受到質疑。記者經常談到事物「表象」或「外觀」,讓事物的實際」本質「變得模糊不清。[17]沃爾福德同樣指出了故事那句強有力但充滿問題的開場白的重要性——「他們都不知道天空的顏色」——為故事的不安和不確定感奠定了基調。[18]
生存與團結
編輯切斯特·沃爾福德(Chester Wolford)在對克萊恩的短篇小說的批判分析中指出,儘管作者最熟悉的主題之一是探討人物在冷漠宇宙中看似微不足道的存在,但因為克萊恩與故事有明顯的聯繫,記者在《海上扁舟》中的經歷可能比之前故事描述的更加個人化。[19]塞爾吉奧·佩羅薩(Sergio Perosa)同樣說明了克萊恩如何「將真實事件轉變為存在主義戲劇,並為簡單敘述中的人類生存鬥爭賦予普遍意義和詩意價值」。[20]
面對最終冷漠的自然,書中的人物們在團結中找到了慰藉。[21]他們經常被合稱為「這些人」,而不是根據他們的職業單獨稱呼,這讓他們之間創造了一種默契的理解,使他們感到彼此的團結。[22]第三節的前幾句話證明了這種聯繫:「很難描述這種在大海上建立起來的微妙的手足之情。沒有人說過是這樣,也沒有人提到過。但它存在於船上,每個人都感覺到了它的溫暖。他們是船長、加油工、廚子和記者,他們是朋友,是超乎尋常地聯結得更緊密的朋友」。[23]生存本身也是一個重要的主題元素,因為這取決於這些人是否能為了拯救自己而與自然作鬥爭。記者的求生欲望體現在他反覆吟唱的歌詞中:「如果我要被淹死——如果我要被淹死——如果我要被淹死,那麼,統治大海的七位瘋狂的神啊,為什麼我被允許走到這麼遠,看着那些沙子和樹木呢?」[24]通過不斷地重複,記者在儀式化地表達自己,但他在存在上仍然漂泊不定。[22]
憐憫
編輯作者伯特·班德(Bert Bender)在其1990年出版的《海洋的弟兄:從莫比·迪克至當代美國海洋小說傳統》中指出,克萊恩對加油工比利的刻畫充滿同情心,他是四個人物中身體最強壯的一個,但卻是唯一死去的一個。記者甚至驚奇地注意到,儘管比利在船沉沒前已經輪班工作兩輪,但他仍具有非凡出色的划船能力。[25]班德寫道,克萊恩「強調比利穩定、簡單的勞動是他在這裡扮演救世主角色的有形基礎」,而加油工被描繪成一個「簡單、勤勞的海員,清楚地表達了他對美國海洋小說傳統中,至關重要的桅杆前海員這一民主理想的同情。」[26]然而,比利未能在這場災難中倖存下來,這一情況與達爾文主義是對立的,因為唯一未能倖存的人恰恰是身體最強壯的人。[27]
A Soldier of the Legion lay dying in Algiers,
There was lack of woman's nursing, there was dearth of woman's tears;
But a comrade stood beside him, and he took that comrade's hand,
And he said, "I shall never see my own, my native land".
外籍軍團的一名士兵躺在阿爾及爾奄奄一息,
這裡沒有女人的照料,也沒有女人的眼淚;
但一位戰友站在他身邊,握着他的手,
他說:「我再也看不到,我的家鄉了。」
《海上扁舟》直接引用了卡羅琳·諾頓夫人1883年創作的詩《萊茵河畔賓根》,該詩重點講述了一名遠離家鄉的法國外籍兵團士兵死亡時緊握戰友的手的場景。記者在回憶這首詩時,看到這位士兵的悲慘境遇與他自己的處境如出一轍,讓他對這位匿名的詩中人物感到難過。愛德華·斯通(Edward Stone)和馬克斯·威斯布魯克(Max Westbrook)等評論家注意到垂死的士兵和遭遇海難的記者之間的相似之處,認為是記者的這個領悟使得他發現在這個冷漠的世界中人與人之間同情存在的必要性。[29]雖然文學上的參考可能被認為具有諷刺意味、缺乏同情心並且只是次要的興趣點,但斯通認為這首詩也可能是《紅色英勇勳章》的來源之一,該書也探討了人與形而上學的關係。[30]
評價及遺產
編輯《海上扁舟》是克萊恩被討論最頻繁的作品之一,經常被編入選集中。威爾遜·福利特將這個故事收錄在他1927年出版的克萊恩作品集第十二卷中,同時還出現在羅伯特·斯托爾曼(Robert Stallman)1952年出版的《斯蒂芬·克萊恩全集》(Stephen Crane: An Omnibus)中。[31]這個故事及其隨後的同名系列作品獲得了當代評論家和作家的高度讚譽。記者哈羅德·弗雷德里克在為《紐約時報》撰寫的評論中讚揚了這個故事的價值,以及斯蒂芬的朋友將其收錄並編撰為作品集的文學重要性:「即使他沒有寫過其他任何東西,《海上扁舟》也足以讓他毫無疑問地在現在的位置上站穩腳跟」。[32]英國詩人羅伯特·布里奇斯在雜誌《生活》的評論中同樣讚揚了這個故事,稱克萊恩「已將這段經歷不可磨滅地定格在你的腦海里,這是對文學工匠的考驗」。[33]美國新聞工作者兼作家哈利·埃斯蒂·杜恩斯(Harry Esty Dounce)稱讚這個故事的情節看似簡單,但它是克萊恩的巔峰之作,在為《紐約晚間太陽報》的撰文中稱,「對於那些讀過《海上扁舟》的人,相比故事的技巧性結構,他們會更深刻地記住那一天四人所經歷的長久且痛苦的掙扎、近在咫尺卻無法觸及的陸地、堅持不懈排水的行為、小心翼翼而又頻繁變換位置來保持平衡的努力、可怕而又穩定的樂觀情緒以及所形成的特殊的小團體兄弟情誼。」[34]
克萊恩在28歲時因肺結核英年早逝,他的作品在他去世後卻重新獲得了人們的喜愛和關注。作家兼評論家阿爾伯特·哈伯德在《菲利士人》雜誌上為克萊恩撰寫了一則訃告,內容中寫到,《海上扁舟》是「有史以來最嚴肅、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現實主義作品」。[35]編輯文森特·斯塔瑞特(Vincent Starrett)還注意到故事中使用的令人沮喪的現實主義風格,他說:「這是一幅荒涼的畫面,而這個故事是我們最偉大的短篇小說之一。」[36]作者的另一位朋友H·G·威爾斯寫道,「《海上扁舟》毫無疑問是克萊恩所有作品中的巔峰之作。」[1]威爾斯在談到克萊恩在寫作中對色彩和明暗對照的運用時說道:「它具有早期故事的所有鮮明力量,同時還帶有新的克制元素。色彩一如既往地飽滿,甚至更加豐富和強烈,但在《紅色英勇勳章》中的那些雜亂無章、令人感到困惑的色彩,都在《海上扁舟》中得到調整和控制了。」[1]這個故事至今仍然受到評論家們的推崇。托馬斯·肯特(Thomas Kent)將《海上扁舟》稱為克萊恩的「代表作」,[37]而克萊恩傳記作家斯坦利·韋特海姆(Stanley Wertheim)則稱其為「克萊恩最優秀的短篇小說和十九世紀末美國文學的傑作之一」。[10]
引文
編輯- ^ 1.0 1.1 1.2 Weatherford (1997), p. 271
- ^ Wertheim (1994), p. 232
- ^ Wertheim (1994), p. 233
- ^ Wertheim (1994), p. 234
- ^ Wertheim (1994), p. 236
- ^ Davis (1998), p. 187
- ^ Wertheim (1994), p. 240
- ^ Sorrentino (2006), p. 191
- ^ Crane (1898), p. 3
- ^ 10.0 10.1 10.2 Wertheim (1997), p. 248
- ^ Crane (1898), p. 52
- ^ Schaefer (1996), p. 302
- ^ Wertheim (1997), p. 27
- ^ Bender (1990), p. 75
- ^ Wertheim (1997), p. 249
- ^ Crane (1898), p. 44
- ^ Halliburton (1989), p. 238
- ^ Wolford (1989), p. 18
- ^ Wolford (1989), p. 17
- ^ Schaefer (1996), p. 315
- ^ Dooley (1994), p. 68
- ^ 22.0 22.1 Wolford (1989), p. 19
- ^ Crane (1898), p. 16
- ^ Crane (1898), pp. 25, 36, 43
- ^ Halliburton (1989), p. 246
- ^ Bender (1990), p. 69
- ^ Wertheim (1997), p. 150
- ^ Crane (1898), pp. 45–46. Two lines of Norton's first stanza ("But a comrade stood beside him, while his lifeblood ebbed away,/And bent with pitying glances, to hear what he might say") are missing in Crane's quotation, and it is disputed whether Crane accidentally misquoted or deliberately truncated the verse. (Jackson, David H. Textual Questions Raised by Crane's 'Soldier of the Legion'. American Literature. 1983, 55 (1): 77–80. JSTOR 2925884. doi:10.2307/2925884.)
- ^ Schaefer (1996), p. 300
- ^ Schaefer (1996), pp. 302–303
- ^ Schaefer (1996), p. 296
- ^ Weatherford (1997), p. 216
- ^ Wertheim (1994), p. 305
- ^ Current Opinion, Volume 62. Current Literature Pub. Co., 1917.
- ^ Weatherford (1997), p. 265
- ^ Starrett (1921), p. 11
- ^ Kent (1986), p. 145
參考資料
編輯- Bassan, Maurice. 1967. Stephen Crane: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Inc.
- Bender M, Bert. 1990. Sea-Brothers: The Tradition of American Sea Fiction from Moby-Dick to the Present.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Crane, Stephen. 1898. The Open Boat and Other Tales of Adventur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New York: Doubleday & McClure Co.
- Davis, Linda H. 1998. Badge of Courage: The Life of Stephen Crane. New York: Mifflin. ISBN 0-89919-934-8.
- Dooley, Patrick K. 1994. The Pluralistic Philosophy of Stephen Cran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ISBN 0-252-01950-4.
- Halliburton, David. 1989. The Color of the Sky: A Study of Stephen Cran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SBN 0-521-36274-1.
- Hoffman, Daniel. 1971. The Poetry of Stephen Cran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ISBN 0-231-08662-8.
- Kent, Thomas. 1986. Interpretation and Genre: The Role of Generic Perception in the Study of Narrative Texts. Lewisburg: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 Schaefer, Michael W. 1996. A Reader's Guide to the Short Stories of Stephen Crane. New York: G.K. Hall & Co. ISBN 0-8161-7285-4.
- Sorrentino, Paul. 2006. Stephen Crane Remembered.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ISBN 0-8173-1503-9.
- Starrett, Vincent. 1921. "Stephen Crane: An Estimate". Men, Women and Boats. New York: Boni and Liveright.
- Weatherford, Richard M. 1997. Stephen Crane: The Critical Heritage. New York: Routledge. ISBN 0-415-15936-9.
- Wertheim, Stanley. 1997. A Stephen Crane Encyclopedia.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ISBN 0-313-29692-8.
- Wertheim, Stanley and Paul Sorrentino. 1994. The Crane Log: A Documentary Life of Stephen Crane, 1871–1900. New York: G. K. Hall & Co. ISBN 0-8161-7292-7.
- Wolford, Chester L. 1989. Stephen Crane: A Study of the Short Fiction.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ISBN 0-8057-8315-6.